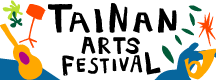南島十八劇場《鯨之駅》
舞臺下的觀眾們被牽引的不應僅是看似理所當然的人生百態與情緒糾纏,更希望創作者筆下、舞臺上的人物們能夠長成更完整的模樣,用著飽滿的生命與面貌,述說著藏身於龐大宇宙萬物中的渺小自我,還有這古老悠久城市裡的故事,正如鯨魚在遙不可及的深海中唱歌,牽動著頻率相同的萬物。
能祖將夫群讀音樂劇《銀河鐵道之夜》
這個製作排練計劃,發生於日本,與社會文脈水乳交融,可是,移植台灣之後,宮澤賢治生活過的大正、昭和時代,相關的社會氛圍和世界觀,對於大部分的台灣演員(包括觀眾)而言,具有多少客觀認知、與主觀感情經驗,如何建構舞台時空和戲劇情境,加上工作時間的短暫,對於表演文本的內化與外顯,都應該會有影響。
能祖將夫群讀音樂劇《銀河鐵道之夜》
我們看到結尾都無從得知,那越是輕易淡忘、就越容易重演的災難,具體指的究竟是什麼?當戲中的災難失去現實的指涉,當我們感受不到詩意的對白在暗示著惘惘的威脅,當詩失去了只有它才能輕輕舉起的沉重,那麼說到底,必須是詩的理由是什麼呢?
辛辛那提大眾管弦樂團《好萊塢璀璨之夜》
富喜感指揮羅素在舞台上充滿熱情的舞動著,令人在欣賞的過程不得不把視線投向他。羅素不時抹一把在額頭上滾動的汗珠,緊湊的一曲接一曲,牢牢抓住每個音符的開始和終結,節奏精確不拖拉,每個樂句的導入、帶動與完結,毫不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