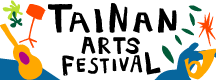雞屎藤新民族舞團《許丙丁文學舞蹈劇場──府城仙怪誌》武德殿版
當《府城仙怪誌》移師至新化武德殿這樣的小型室內空間,在武德殿內、外轉變觀看的動線則加強了劇情中女主角由昭和時代進入仙怪世界的氛圍,而且讓觀眾得以近距離接觸舞臺空間,有助於觀賞布袋戲偶和舞者的演出細節,但是也因為場地的限制,讓舞者的演出空間明顯受到壓縮。
南島十八劇場《鯨之駅》
舞臺下的觀眾們被牽引的不應僅是看似理所當然的人生百態與情緒糾纏,更希望創作者筆下、舞臺上的人物們能夠長成更完整的模樣,用著飽滿的生命與面貌,述說著藏身於龐大宇宙萬物中的渺小自我,還有這古老悠久城市裡的故事,正如鯨魚在遙不可及的深海中唱歌,牽動著頻率相同的萬物。
雞屎藤新民族舞團《許丙丁文學舞蹈劇場──府城仙怪誌》武德殿版
為了讓觀眾可以神遊其中,仙怪舞者們的造型相當有特色,甚至還有戴墨鏡,手持鈴鐺的馬扁禪師。由於舞者們沒有台詞,單純靠著肢體動作來展現戲劇性。也因此,戲偶師傅在劇中以說書人的身分穿針引線,顯得更加重要。
能祖將夫群讀音樂劇《銀河鐵道之夜》
這個製作排練計劃,發生於日本,與社會文脈水乳交融,可是,移植台灣之後,宮澤賢治生活過的大正、昭和時代,相關的社會氛圍和世界觀,對於大部分的台灣演員(包括觀眾)而言,具有多少客觀認知、與主觀感情經驗,如何建構舞台時空和戲劇情境,加上工作時間的短暫,對於表演文本的內化與外顯,都應該會有影響。
能祖將夫群讀音樂劇《銀河鐵道之夜》
我們看到結尾都無從得知,那越是輕易淡忘、就越容易重演的災難,具體指的究竟是什麼?當戲中的災難失去現實的指涉,當我們感受不到詩意的對白在暗示著惘惘的威脅,當詩失去了只有它才能輕輕舉起的沉重,那麼說到底,必須是詩的理由是什麼呢?